“格根鲍尔转变”概念最初由整体论-有机论生物哲学家阿道夫·迈耶(-阿比希)(Adolf Meyer(-Abich) 1893-1917)在其1934年广受阅读的生物学公理化中提出。该术语迅速被民族有机论植物学家、理想主义形态学家及歌德科学著作编辑威廉·特罗尔(Wilhelm Troll)采纳,他在1937年的教科书中批评了以系统发育为动机的形态学是一种范畴错误。瑞士动物学家、唯心主义形态学家阿道夫·内夫(Adolf Naef)在1926年发表的对同源概念批判性评论中指出:“1870年(其《基础》第二版出版之年),在海克尔影响下,格根鲍尔完成了向系统发育学家的转变。”整体论/有机论者及新拉马克主义功能解剖学家汉斯·伯克尔(Hans Böker 1886-1939),曾是罗伯特·维德尔斯海姆(Robert Wiedersheim 1848-1923)在弗莱堡阿尔伯特-路德维希大学研究所的同事,后于1932年成为耶拿大学解剖学研究所的全职教授兼所长,他赞扬了格根鲍尔《基础》第一版(1859年),因为它为比较解剖学及其身体构造概念(Bauplan)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精确与简洁——“但无人敢于断言身体构造与血缘关系之间可能存在联系。”这一情况随着1870年格根鲍尔《基础》第二版的出版而改变:在此版中,身体构造成为血缘关系的证据,比较解剖学演化为进化形态学,整个研究的目标转变为以反映系统发育关系的方式重建自然系统。
马克斯·福尔布林格(Max Fürbringer 1846–1920),格根鲍尔曾经的学生和助手,后来成为耶拿大学教授,并最终接替格根鲍尔在海德堡大学的职位,他这样形容已故导师的研究计划:“无一物脱离其自然脉络,万物生机盎然,通过因果与关联的生命原则彼此渗透、统一。” 此处,“因果”指系统发育框架,“关联”则指比较解剖学,或更具体地说,是同源关系。“理论替代” 将唯心主义形态学或类型学替换为系统发育形态学,不仅需要解释如何将抽象(即不受时空限制)的概念如类型转化为时空定位的实体如祖先物种,还需阐明结构对应如何能支持因果推理。同源是一种共存关系,而因果——至少在系统发育中——是一种后继者的关系。 据格根鲍尔自己承认,他向达尔文主义及由此导向的进化形态学的转变,不仅归功于布隆翻译的达尔文“名著”,而且——或许更多——归功于海克尔《普通形态学》第二卷的第19章和第20章。海克尔的单一论无疑影响了他,同样,海克尔坚持认为生物过程——无论是谱系的还是生理的——都应仅基于机械因果律来解释,无需诉诸有机论和目的论原则。然而,格根鲍尔的思想浸透着海克尔式的进步主义,认为一切发展——无论是胚胎的还是进化的——都遵循规律向更高层次的复杂性和完美性攀升。格根鲍尔还深受海克尔强调实证研究重要性的吸引,认为这是强大归纳的基础,能够导向自然法则的建立,尽管他比海克尔更犹豫是否赋予这些生物法则,特别是进化(即历史)转变的法则,与物理(力学)法则同等的定律地位。格根鲍尔对变异和遗传问题鲜有评论,但他确实赞同海克尔的观点,认为自然选择驱动物种转变,并推动向完美进化的规律性进程。在他看来
血缘理论将在比较解剖学的历史上开启一个新时代。该理论将标志着这一科学领域比以往任何理论所引发的更为重大的转折点。血缘理论比任何其他比较解剖学理论都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以至于形态学中没有任何一个方面不会受到其最密切的影响。
尽管在《比较解剖学基础》(1874年版的《纲要》)的不同版本中触及了深层次的哲学问题,格根鲍尔最为简洁地处理这些问题是在1876年,他在自己创办的新期刊《形态学年鉴》第一卷的导言中阐述了这些观点。该期刊由莱比锡的威廉·恩格尔曼(Wilhelm Engelmann)出版,专注于解剖学与发展史的研究。格根鲍尔强调,在形态学科学中,“对局部的考量增进对整体的理解,正如整体加深对局部的理解”:这是一种诠释循环,旨在描绘归纳与演绎如同分析与综合那样紧密交织——或应当如此。与其他所有科学一样,形态学分析的第一步是描述性的,因此也是分析性的。但这不能是最后一步,而必须导向一种比较方法,这构成了形态学研究的综合部分。这一综合步骤至关重要,因为其目标是揭示形态对应中的因果关系,即同源性。**同源性因此不再被理解为单纯的对应关系,而是被解释为指示共同祖先的因果关系。**达尔文主义在格根鲍尔手中并未激发变异或适应性的研究,而是为旧有的研究计划——即经典(唯心主义)比较形态学——提供了新的理论,也就是解释性的基础,正如达尔文所预言的那样。根据进化论,人们不能再接受每个物种或每种身体构造是特别创造的,每个都是神圣理念的体现。相反,必须假设物种及其所体现的身体构造通过血缘关系相互关联。形态转变的进化因果关系,在寻求生物体、其器官复合体或器官基于形态条件所体现的序列排列中的一致性时,通过尽可能广泛地撒下形态比较之网,得到了最佳揭示。
凡是在精确比较的基础上,我们能识别出组织结构上的对应关系,这种基于遗传的对应关系便表明共同祖先的存在。然而,这样的比较绝不应局限于单一、任意选取的器官。相反,生物体必须在它们的所有部分中体现出谱系关系的可能性。
进化形态学家因此被要求在比较分析中避免专注于单一器官或器官系统。通过证据的一致性,即源自尽可能多器官或器官系统比较分析的证据,对共同祖先的推论得以加强。代表同一类型的生物体的器官或器官系统越多,沿着彼此平行的转化序列排列,形态学证据能够因果关系(即历史性解释)的推论就越强。将形态转化解释为系统发育过程的结果,预设了遗传机制的存在,然而这些机制尚属未知,这使得所有基于遗传的解释都极具推测性。但格根鲍尔认为,如果科学推理被束缚于避免所有假设性推论的要求上,科学将无从谈起。 血统理论以普遍因果关系原则支撑比较形态学,而比较形态学的成功则为支持血统理论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格根鲍尔将解剖学视为分析和描述性的;相比之下,比较解剖学则是综合性的,其目标是将生物体及其部分排列成连续的形式系列,从而推断出潜在的转化过程。根据迈耶(-阿比希)的观点,格根鲍尔转化中的关键步骤在于,通过从这样的系列推断出潜在的历史转化过程,将器官、器官系统或生物体(在其发育的任何阶段)的理想排列替换为连续、不间断的形式条件系列。对于迈耶(-阿比希)而言,纯粹理想化、类型学构想的形式条件系列是一种脱离时间的逻辑构造,因此缺乏方向性:可以从任一方向解读。但如果将这一系列形式条件解释为历史转化的结果,情况则不同。此时,时间箭头规定了解读系列的唯一方向。 在格根鲍尔看来,转化系列依法从简单向复杂、从原始形态向衍生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组织水平演进。 对潜在系统发育过程的假设,为通过归纳法推断出支配这些转化系列的规律提供了平台。一旦这些规律通过归纳得到确证,比较解剖学便因获得演绎基础而臻于成熟。
比较解剖学致力于从事件中推导形态条件,并渴望发现支配这些事件的法则。即便这些法则或许尚不能用数学语言精确表述,其科学内容的重要性相对于其他科学(如物理学和生理学)而言或许会有所调整,但在其自身学科领域内却不容置疑。任何异议观点同样必须质疑其他历史学科,甚至如(历史)地质学这样的自然科学之科学地位。
如果形态学这门科学能够获取地球上现存及曾经存在的所有生物形态以供比较,它理应能够以符合它们历史的方式将这些形态联系起来,即以一种反映生命之树的方式。遗憾的是,这些形态并不齐全,尤其是化石记录,至今仍令人遗憾地不完整。
如果所有曾经存在的形态都能用于比较,“许多谜题将迎刃而解,但形态学这门科学却会因此失去其理论意义,”格根鲍尔坚持这样认为。 因此,理论上的连续且不间断的形态序列中的经验空白,必须通过概念来填补。在比较形态学中,必须先确立对形态多样性的概念理解,才能援引系统发育上的,即基于因果关系的转变。 “在感官经验无能为力之处,组合性的智力活动必须开始”:填补生物体之间、它们的器官以及器官复合体之间形态学空白的工具,是同源关系。正是在同源性的定义中,格根鲍尔的转变论措辞最为显眼,也最具争议性。在定义“特殊同源性”或“严格意义上的同源性”时,他继续引用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但现在的定义与他《基础》第一版中的表述大相径庭:
我们称此为两个器官间的关系,它们同源,因而源自同一胚胎原基(Anlage)。特殊同源性不同于之前提到的所有其他类型的同源性……在于这里的比较需要详细证明系统发育关系(da die Vergleichung hier genaue Nachweise der verwandtschaftlichen Beziehungen erfordert)……证明特殊同源性是比较解剖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格根鲍尔在其下一部比较解剖学著作中澄清了他新定义的同源性与之前使用这一概念的显著区别,这部著作是他《基础》一书的简略版,现称为《比较解剖学概要》,于1874年出版。在前达尔文时期,即歌德式唯心主义形态学谈论关系时,所隐含的仅是一种唯心形态上的联系。相反,他新定义的同源性则暗示了血缘关系,他主张:“我们因此用关系的概念替代了组织结构对应或一致性的概念……生物关系的科学,即进化论或系统发育学,建立在遗传法则之上。” 若前达尔文时代的理论家将目的论注入胚胎发育的解释中,现在则被系统发育的解释所取代。源自同一胚胎原基继续为特定同源性提供关键线索,但格根鲍尔再次令人困惑地指出:“寻找特定同源性需要精确验证系统发育关系。” 对于他的读者和批评者而言,这个在1878年第二版《概要》中以不变措辞重现的问题在于,格根鲍尔的定义似乎暗示要检测特定同源性,需预先了解系统发育关系。这有本末倒置之嫌,因为同源性本应指示系统发育关系,而非相反。格根鲍尔真正想表达的是,同源性与祖先关系处于一种相互阐明的关系中,再次依赖于证据的一致性。这一点在他最成熟的作品,即去世前三年出版的1898年《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中变得显而易见。
“比较解剖学的任务与目标在于系统发育,以及随之揭示生物间普遍存在的规律性关系”;比较解剖学研究器官的历史,并通过所有器官的总和,探究生物体的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解剖学是一门与地质学同等重要的历史科学。 确实,带有变异的遗传并非直接可见,但从理论前提出发得出结论是所有科学的特征。在比较解剖学中,这些前提建立在三类观察事实之上:生物间器官及器官系统的结构对应性;器官或器官系统源自相应的胚胎原基;以及尽管不完整,但提供了“相当有力论据”的化石记录。
结构对应与胚胎起源仍是同源性的关键,但:
为了展示某一器官的同源性,对所考察生物其余系统发育关系的考量至关重要;因为同源关系受共同祖先支配,同源器官源自同一源头,它们要么从共同原始形态偏离至相同程度,要么一个偏离较多,另一个偏离较少……任务之所以更加复杂,是因为如果一个生物体向更高复杂性层次进化,并不意味着其所有器官会[同时]达到这一分化水平。在较高复杂性层次上,某一器官可能仍保持较低形态,同样,在较低复杂性层次上,特定器官可能展现出较高的分化程度。因此,需要极其谨慎以避免得出错误结论。
格根鲍尔在此所述,将揭示一个极为根本的见解,这一见解将在未来系统发育学的发展中占据核心地位。依据他的观点,同源器官——能够推断共同起源——源自相同的祖先形态条件,这一条件要么通过它们从相应胚胎原基发育而来的过程得以展现,要么通过它们在成体生物中的拓扑和连接性对应关系重建,或两者兼而有之。由于同源性受系统发育支配,根据进步律推导出的预测是,比较生物体所考虑的所有器官将一致地显示出向更高复杂性趋同的进步。换言之,比较生物体所考虑的各种器官的转化系列将彼此平行发展。然而,情况并非必然如此,因为格根鲍尔认识到,某些器官在系统发育过程中可能超越或落后于其他器官。这一见解的推论是,尽管胚胎发育的比较研究确实能阐明形态学比较,“但所有将胚胎学誉为照亮解剖学明灯的说法都必须极为谨慎地对待。” 系统发育不能简单地从胚胎发育中窥见,这是格根鲍尔在其漫长职业生涯中日益强调的警示。
器官或器官系统如此不均衡的发展,体现在根鲍尔为其“鳃弓理论”(gill arch theory)辩护,反对与之竞争的“侧鳍褶理论”(lateral fin-fold theory)上。 “侧鳍褶理论”认为脊椎动物的成对附肢是通过分隔和分化,分别从假设存在于祖先形式腹侧体边缘的原始连续鳍褶的前后端演变而来。而根据根鲍尔的观点,脊椎动物的成对附肢是由沿躯干后移的鳃弓进化而来。鳃弓自身会转变为内骨骼的胸带和骨盆带元素,鳃耙则演化为鳍的内骨骼支撑结构(辐条)。根鲍尔的“鳃弓理论”基于一个假设,即在鱼类中观察到的各类鳍结构中,原鳍型是最原始的一种。与后鳍型——如鲟鱼( Acipenser )、弓鳍鱼( Amia )、雀鳝( Lepisosteus )及硬骨鱼(如鲑鱼或鳟鱼)所见宽基“扇形”鳍结构——相比,原鳍型的特点在于其狭窄的基部支撑着一个向外指向的轴,轴上带有前轴和/或后轴辐条。在现存脊椎动物中,原鳍型以腔棘鱼、肺鱼和四足动物为代表,但也见于腔棘鱼的化石近亲、化石肺鱼以及一些古生代鲨鱼中。 1879年,根鲍尔在其《形态学年鉴》中发表了其学生兼助手米哈伊尔·冯·达维多夫(Michael von Davidoff,)关于鱼类腹鳍比较解剖学的专论。达维多夫试图证明腹鳍在系统发育转变中较为保守,即其进化比胸鳍更为稳定。这意味着在鱼类渐进进化过程中,腹鳍在进化转变和进步方面会落后于胸鳍。因此,腹鳍更接近祖先生物形态,相较于胸鳍,在讨论脊椎动物成对附肢起源时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然而,在论文的开篇部分,达维多夫表明自己支持根鲍尔关于脊椎动物成对附肢起源的观点,并以此为由,拒绝进一步评论对立观点,转而引用了根鲍尔的相关论文。
在评论其学生的研究时,格根鲍尔通过提及蝾螈为后者的结论提供了额外支持,指出蝾螈的足部保留了原始的五趾特征,而手部则仅剩四趾。他还指出,翼龙、鸟类和蝙蝠的前肢演化为翅膀,这些动物的后肢结构相对保留了较为原始的状态。 但这并非他撰写附言的唯一动机。相反,他想要评论“侧鳍褶理论”,这一理论在他关于脊椎动物成对附肢起源的思考中此前未曾扮演任何角色,因为他最近才通过“巴尔弗的卓越研究”了解到它。 “侧鳍褶理论”通常与英国形态学家弗朗西斯·梅特兰·巴尔弗(Francis Maitland Balfour 1851–1882)和美国人詹姆斯·K·撒切尔(James K. Thacher 1847–1981) 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们是首批挑战格根鲍尔“鳃弓理论”的学者。格根鲍尔强调,他的研究基于鲨鱼,他认为鲨鱼是最原始的现存有颌类动物。相比之下,撒切尔则以鲟鱼为研究对象,而格根鲍尔认为鲟鱼是一种更为进化的鱼类。格根鲍尔坚信鲨鱼的鳍最接近假想的祖先状态,但他也承认,对于鲟鱼而言,“认为它们的所有器官系统都表现出更高的分化程度是错误的。”因此,至少应考虑这种可能性:尽管鲟鱼在许多器官系统上相对于鲨鱼显示出更大的进化程度,但在脊柱结构上并非如此,同样在鳍的结构上也可能没有。 与鲨鱼相比,鲟鱼因此展示了一种器官分化的镶嵌模式,有些器官进化较快,其他则滞后。事实上,格根鲍尔也承认,在他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器官进化也存在类似的不一致。现存鲨鱼——他最初基于这些鲨鱼提出“鳃弓理论”——没有显示出原始鳍。相反,现存鲨鱼拥有宽阔的鳍,乍看之下,这似乎为“鳍褶理论”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支持。格根鲍尔认为“鳍褶理论”最令人难以接受的含义是(内)骨骼元素(肢带元素和鳍支撑结构)的新生形成及其组合形成一个结构和功能单位,“这两个假设步骤从未获得任何观察基础。 然而,他本人关于原始鳍的初步构想同样缺乏观察基础。原始鳍最初是一个理论构建,格根鲍尔通过一系列预设的复杂转变,从鲨鱼的胸鳍和腹鳍形态中推导出来。 怀着建立涵盖鳍与四足动物四肢统一蓝图的愿望,格根鲍尔转向了其他鱼类,这些鱼类能够以比现存鲨鱼更自然的方式代表原始鳍,并发现肺鱼, 尤其是新角齿鱼 Neoceratodus , 正是如此。这意味着,他认为在组织水平上远超鲨鱼的一类鱼类,却最接近祖先的鳍结构。又一次,一种在他看来高度进化的鱼类,其成对附肢却保留了原始结构。
鉴于格根鲍尔的进步主义观点,此讨论暗示,任何具体生物体,因其体现某种组织结构类型,可能由在复杂性与完善性上升阶梯上更为或较不先进的器官或器官系统构成。因此,一个假想的形态祖征不能仅从胚胎中直接读出,而最终必须基于比较解剖学进行推断。这就是为什么,在格根鲍尔看来,比较胚胎学永远无法使比较解剖学变得多余。格根鲍尔的这一结论反映了十九世纪末德国生物学中进化形态学普遍存在的争论或冲突。 格根鲍尔识别出两种能够引导同源性认知的线索——比较解剖学与个体发育,即器官源自相应胚胎原基的过程。这场冲突或争论,焦点在于这两条线索中哪一条应被赋予更高的认知优先权。格根鲍尔从理想主义转向进化驱动的形态学,无疑深受海克尔的影响,后者通过阐述个体发育、系统发育与化石记录之间的关系,在生物学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转向海克尔。
本章节是对 Phylogenetic Systematics: Haeckel to Hennig 的部分翻译,如果有出版社感兴趣,欢迎联系 malacology.net ,版权所有禁止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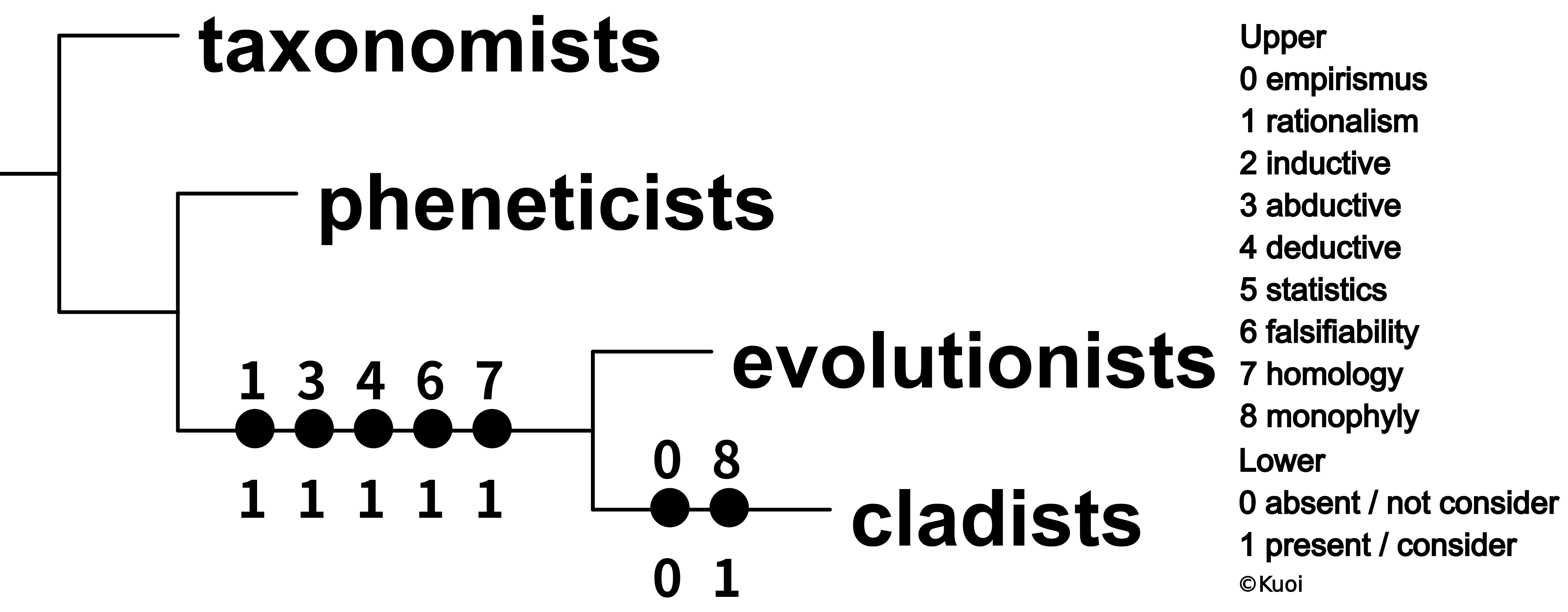

Comments
No comments yet. Be the first to re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