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斯特·海克尔是一位个性鲜明且极具影响力的德国生物学家,在德国生物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对民族主义传统下尤其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兴起负有责任。他在世时在生物科学领域的影响巨大;其遗产将影响德国生物学长达数十年。不仅如此,海克尔还积极投身于哲学、社会、宗教和政治辩论中,在一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看来,这些行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生活中的每一个片段,科学领域的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被叙述、评论、解读并引发争议。 恩斯特·海因里希·菲利普·奥古斯特·海克尔(Ernst Heinrich Philipp August Haeckel)于1834年2月16日出生在波茨坦。他的父亲卡尔·戈特洛布(Carl Gottlob)是一位高级公务员(政府顾问),母亲夏洛特·塞特(Charlotte née Sethe)来自律师世家。1835年,海克尔一家迁至梅泽堡,恩斯特在那里完成了小学和中学教育,为接受大学教育打下了基础。在父母家中,海克尔接触到了政治辩论,同时被鼓励培养对旅行、文学和自然历史的兴趣。1852年春季,海克尔开始在柏林学习医学,但为了在1852/53年冬季学期跟随弗朗茨·莱迪希、尔伯特·冯·科利和克鲁道夫·菲尔绍学习,他转到了维尔茨堡大学。特别是菲尔绍强调生物组织的细胞层面(菲尔绍的细胞病理学及其关于生物体构成细胞国家的观点)对海克尔产生了持久影响,海克尔曾一度担任其科研助手。1894年2月16日,海克尔60岁生日之际,他回忆道,菲尔绍将科学与哲学相结合的倾向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将精神现象归结为物质过程的观点。 可能是听从了格根鲍尔的建议, 海克尔于1854年春季返回柏林,在约翰内斯·穆勒门下学习解剖学和生理学。海克尔一生都对这位杰出的科学家怀有敬仰之情,穆勒曾带他前往赫尔戈兰岛沿海水域,向学生展示了海洋生物学的丰富世界。约翰内斯·穆勒的远洋捕捞方法在日后对海克尔大有裨益,为他史诗般的海洋浮游生物研究提供了材料。同样在柏林,海克尔聆听了植物学家亚历山大(卡尔·海因里希)布劳恩(Alexander (Carl Heinrich) Braun 1805-1877)的讲座,后者影响了他对物种和生物个体性的看法。1857年,海克尔通过了博士学位考试,并在意大利之行后,于1861年在耶拿大学获得授课资格(Habilitation),这得益于卡尔·格根鲍尔的建议和支持。海克尔随后在耶拿大学开启了非凡的学术生涯,直到1909年,期间频繁游历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并进行了几次遥远的热带海岸探险——这些探险秉承了伟大的亚历山大·冯·洪堡的精神,并以“透过蓝色的德国童话之眼”艺术地描绘出来。1882/83年间,海克尔参与了耶拿大学自主动物学研究所的创建;由海克尔创立的耶拿系统发育博物馆于1907/08年建成。海克尔于1919年8月9日在耶拿的“美杜莎别墅”(现为恩斯特-海克尔故居)中去世。
海克尔最初是通过德国古生物学家海因里希·G·布朗(Heinrich G. Bronn)于1860年出版的达尔文《物种起源》译本了解到达尔文的作品。同年,布朗在德国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矿物学家广泛阅读的月刊《矿物学、地史学、地质学与化石学新年鉴》(Neues Jahrbuch für Mineralogie, Geognosie, Geologie und Petrefakten-Kunde)上发表了对达尔文《物种起源》的批评性评论。布朗对达尔文的评论发表在他对化石在地壳中规律分布进行了重大研究之后的两年,其著作《有机世界的演化法则》(Entwicklungs-Gesetze der organischen Welt)被译为英文摘要。该论著包含了自然系统的图形表示,并通过化石记录以分支树状图的形式展示了其与时间维度的关系,虽看似进化树,实则不然。然而,有人认为,布朗及其对自然系统的树状表示在概念上为海克尔接受比较解剖学中的进化观点做好了准备。在评论达尔文的进化论时,布朗指出,证明与反驳同样难以获得。他强调,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解释无生命物质如何产生具有细胞结构的有机物质,以及这种细胞有机物质随后如何转化为低级生物种类的胚芽和卵。他认为,这或许并非不可能,但根据达尔文的解释,可能性极低:“像蝴蝶或马等如此精妙设计至每一根纤维的生物,竟然是盲目的自然力量的产物,这一点仍然令人难以置信。”由此,布朗为未来几十年德国生物学界对达尔文理论的接受定下了基调。自海克尔起,达尔文主义被等同于或简化为自然选择理论,这一彻底外因论的进化解释在德国生物学家中遭遇了许多质疑。
1863年9月19日,海克尔在波兰斯德丁举行的第38届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大会上首次发表了关于达尔文物种起源理论的演讲。 此后,海克尔不遗余力地在科学界和公众中传播进化论,作为达尔文的大使活跃于整个德国乃至欧洲大陆,其热情之高,以至于达尔文本人偶尔提醒他要注意适度。他从“发展思想”中引申出具有争议的社会政治后果,这些思想影响了学校及高等教育的教学计划。海克尔是一位坚定的自由思想家(Freidenker);他坚决反对基于身体与灵魂二元论前提的基督教,并最终于1906年在耶拿大学动物研究所创立了单一联盟(Monistenbund)。随着单一论而来的,还有对科学统一的诉求,对无机物与有机物之间存在鸿沟的否定,以及由社会达尔文主义支撑的世界观统一的宣扬,该主义提倡优生和安乐死措施,并将死刑视为“真正有益” 的人工选择手段。这些主题的升级可以通过海克尔广受欢迎且广泛阅读的《自然创造史》的连续版本来追溯,该书首次出版于1868年,共经历了9个版本,并被翻译成12种语言。在第一版中,关于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第七讲(章节)基本未涉及社会政治内涵。而在1870年的第二版中,狂潮开始涌动,书中将古希腊斯巴达人的健康和活力解释为通过淘汰不适后代的人工选择结果。类似的有利实践也被报道存在于北美印第安土著部落,即海克尔所称的“原始红皮肤人” 中。这与“现代文明国家的衰弱” 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源于“军事选择”,即强壮有能力的士兵为大多无意义的家族纷争等理由战死前线,而体弱无能者留在家中繁衍后代。同样有害的是“医学选择”,它使得“潜伏的遗传恶疾” 得以传播。这些担忧在1872年的第三版中再次被表达,此外,他还谴责那些在容忍战争的同时提议废除死刑作为“自由主义措施”的“人类文明”:“对不可救药的罪犯判处死刑不仅是正当的,也是人类优秀部分的福祉;就如同精心照料的花园中拔除杂草带来的益处一样。” 从精心培育的花园中拔除杂草的比喻,在后来定义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民族传统中,被证明是一个有力且持久的影响。到了1875年的第六版,海克尔又引入了一种有害的人工选择载体:“比医学选择更为危险和毁灭性的是由强大且组织统一的等级制度普遍实施的教会选择过程。” 神职人员数千年来对教育、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的影响导致了“整个文化和习俗的衰败”。他声称,这一点在天主教教会中尤为明显,其历史进程中曾将科学推至前所未有的低谷。
人工选择因此对人类社既有利也有弊,而科学指导下的政治任务便是做出正确决策并加以实施。海克尔论证的重要性在于,他将自然选择学说与一种毫无约束的进步主义结合起来,他设想通过精心设计的人工选择手段,将这种进步主义延续到民族关怀中。海克尔是右翼(民族主义)全德联盟的成员,也是种族卫生学会的荣誉会员,但同时支持国际理解联盟的和平主义努力。他对历史进步坚定不移的信心使他相信,人类大脑的持续进化终将让武装冲突成为过去。鉴于海克尔在科学和大众写作方面极其丰富的出版遗产,他对社会辩论和政治的公开参与,以及他以一位地位崇高的学者身份,基于现代实证科学特别是达尔文生物学的启蒙,所提出的无畏声明,加之他多变的政治和社会立场,对他的工作和影响的历史分析引发高度争议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尤其体现在海克尔作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先驱的角色上。当汉斯·舍姆(Hans Schemm)——一位早期纳粹分子及臭名昭著的国家社会主义教师联盟创始人——将国家社会主义描述为应用政治的生物学时,他回顾了海克尔的言论,海克尔曾宣称政治是应用的生物学。然而,将海克尔描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策划者与纳粹理论家利用甚至滥用海克尔的著作以及支持纳粹生物学的持久影响是完全不同的。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学生,如教育改革家和后来的纳粹思想家保罗·布罗默(Paul Brohmer 1885-1965)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先驱者。正如生物学史学家马里奥·迪·格雷戈里奥(Mario Di Gregorio)所言,“历史上曾周期性地试图寻找应对纳粹和法西斯恐怖负责的历史人物。同样的指责也曾指向理查德·瓦格纳、尼采、黑格尔,甚至马丁·路德。”在更一般的层面上,海克尔确实深受民族主义传统的影响,这种传统被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专家激进化了,尽管未必直接聚焦于海克尔本人及其著作。无论如何,在他自己的时代,海克尔必须捍卫自己,不是以右翼政治或法西斯主义的角色,而是社会主义和学术自由主义的角色。
对他的攻击并非他人所为,正是他在维尔茨堡的前教授鲁道夫·维尔肖,在1877年9月于慕尼黑举行的第59届德国自然科学家与医师大会上发起的。海克尔于9月18日登台发言,其演讲全面展示了他宏大的理论体系。他一开始就纠正了在其巨著《普通形态学》(1866年)中已受批判的范畴错误,坚决摒弃目的论,同时宣称适应是机械原因偶然串联的“必然结果”。他再次强调了“发展理念”的核心重要性,以及这一事实:用历史-谱系学方法取代数学-物理学方法后,唯有进化论一劳永逸地为人类起源提供了完整解释,这不仅涉及身体特征,还包括人类的精神禀赋。他同恩斯特·威廉·冯·布吕克(Ernst Wilhelm von Brücke 1819-1892)一道,将细胞定义为基本有机体,这是他那位声名显赫的老师维尔肖奠定理医学基础的概念。他基于物质基础,将细胞之灵魂定义为原生质中固有的张力。根据他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海克尔宣称灵魂与有机物质在其层次整合的各个层面共存,从“质体微粒”和细胞到构成有机体的复杂整体。他高呼,“发展理念”不仅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统一起来,还将提供一个稳固的自然主义基础,从中可推导出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爱、社会本能及责任感,这些美德不应与教会宗教相混淆。鉴于其核心与统一的重要性,“发展学说”注定要在学校课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我们相信,一场深远的学校改革将不可避免。”最后,海克尔对埃米尔·杜布瓦-雷蒙(Emil Du Bois-Reymond 1818-1896)关于我们对自然经验知识局限性的分析进行了抨击:
进化论所揭示的无限进步前景,同时提供了对近来多方用以反对它的那种令人厌倦的“不可知论”最有力的反驳。鉴于人类智力惊人的发展,无人能预言未来其将超越自然知识的哪些界限。
海克尔在演讲中所展示的内容,大多是他之前已经宣扬或发表过的。9月22日,维尔肖登台发言,彼时海克尔已离开会议。维尔肖引介了曾创立德国自然科学家与医师年会的著名人物洛伦兹·奥肯(Lorenz Oken),将其作为学术教学与研究领域受压迫的受害者,并以此对比当前德国大学中盛行的宽松氛围,这种学术自由中的无度宽容,使得如海克尔这样的教授得以沉溺于毫无科学依据的个人臆想之中。海克尔及其前辈植物学家卡尔·内格利(Carl Nägeli),都曾在这样一场显赫的集会上发表进化论观点,得益于学术自由,但维尔肖警告说,科学家们“应当通过放弃个人嗜好与见解来实践一定程度的克制”——此言一出,赢得了听众的热烈赞同。维尔肖进一步将“学术教学的自由”与“研究计划的推测性扩展”相对比,主张科学的推测性边界属于研究领域,而讲堂则应仅用于传播经验证实的知识。海克尔将进化论如“新宗教”般传播,其大部分内容仍处于未经验证的地带,只有在基础稳固、建筑安全建立之后,才能向更广泛的公众传播。“只有当氢、氧、氮的结合特性如何赋予原生质以灵魂这一点向我阐明时,我才会认为在课堂上引入‘原生质灵魂’这一概念是合理的。”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告诉教师们:不要教授那个!” 维尔肖坚称,海克尔的形而上学思考目前不过是文字游戏。他以“研究自由”不等于“教学自由”的范式作为结论。
以当前仍高度推测性的构成应用于我们的整个世界观、社会与国家,根据维尔肖的观点,进化思想中固有的社会主义倾向使得这一理论对体面构成了巨大威胁。维尔肖将1871年春天在巴黎引发动荡的无产阶级革命骚乱归因于法普战争失败后激进化的社会主义可能带来的后果,这一解释似乎在不久后得到了印证:1878年5月11日,马克斯·赫德尔(Max Hödel 1857-1878)在莱比锡刺杀威廉皇帝未遂;同年6月2日,卡尔·爱德华·诺比林(Karl Eduard Nobiling 1848-1878)在柏林也试图行刺。保守和宗教媒体立即站在维尔肖一边,既赞扬他稳健的保守主义,也庆祝所谓的“猿猴狂热者”——海克尔派——在慕尼黑会议上遭受的挫败。更为进步的媒体如《法兰克福报》则对维尔肖的观点表示遗憾,认为他与海克尔共同支持悬而未决的学校改革立法的机会就此丧失。海克尔则以公开回应维尔肖的方式反击,发表了1878年出版的小册子《自由的科学与教学》。海克尔指责维尔肖试图中止学术教学的自由,并援引普鲁士宪法第20条和德意志帝国宪法第152条,两者均宣称科学与学术教学的自由。在海克尔看来,维尔肖否定细胞灵魂不过是玩弄文字游戏,只能证明他背离了自己细胞病理学核心的机械论原则。海克尔嘲笑维尔肖对严格经验主义的诉求是一种哲学上的天真:“我们对力或物质的真实本质又了解多少呢?”“细胞,”他接着说,是一个抽象概念,而非可观察的实体;可观察的总是这样或那样的细胞,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分化。“那么,细胞理论是否同样应该被逐出课堂?”。海克尔展开了一场广泛的考察,从物理、化学跨越生物学到哲学、历史与语言学,旨在展示任何科学中,所有观察都与理论和推测密不可分。他发现达尔文主义——如果有的话——是贵族式的,而非民主的,当然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但他强调科学应自由发展,独立于任何可能被解读或从中得出的政治含义。
若有人欲将这一英语理论赋予任何政治意涵——这无疑是可能的——那么其内在倾向只能是贵族式的,绝非民主的,更遑论社会主义……因为自然选择理论教导我们,在人类生活中,与动植物界一样,始终只有一小部分特权阶层能够生存并奋斗,而绝大多数人则忍饥挨饿,迟早悲惨地消亡。
海克尔总结时,将菲尔绍在慕尼黑的《限制论》演说定性为杜布瓦-雷蒙《不可知论》演说的精神延续,后者最初是在1872年8月莱比锡举行的第45届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师大会上的发言,他宣称:“如果埃米尔·杜布瓦-雷蒙想要宣扬他的‘不可知论’,如果菲尔绍想要将他的更为极端的‘限制论’作为科学的核心口号,那么让我们从耶拿和其他上百个教育中心以响亮的‘无畏前行’予以回应。” 确实,海克尔在菲尔绍的讲话中识别出的反动幽灵,这促使他加强了对进化论的支持“宣传”,正如他向友人、诗人赫尔曼·阿尔默斯(Hermann Allmers 1821-1902)解释的那样。
一些评论家将海克尔与菲尔绍之间的这次交流的重要性,比作1830年乔治·居维叶与杰弗洛伊·圣伊莱尔(Geoffroy Saint-Hilaire)在巴黎皇家科学院关于比较解剖学手段与目标的那场辩论,那次辩论曾引起国际关注与评论。海克尔的小册子因此被译为法语和英语。海克尔为英文版作序,将菲尔绍对“现代进化论”缺陷的具体攻击视为老生常谈,认为已被多次有力驳斥,无需再讨论。他个人感慨于自己与“曾是其热忱弟子与最热情追随者”的人之间出现的分歧,但随后表达了对一位“在科学与政治进步阵营中长久居于领导地位”的人,竟公开捍卫如此反动立场,甘愿被政客与教士利用来“支持精神倒退”的困惑。在英文版引言中,达尔文的斗牛犬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在海克尔与菲尔绍身上发现了歌德在杰弗洛伊·圣伊莱尔与居维叶身上识别的相同品质:“一个才智富于想象与综合……另一个则实证、批判、分析。”赫胥黎认为双方各有优劣,不得不对“两位杰出的对手引用法国前议院主席那句名言——‘Tape dessus’(给他点颜色看看!)”。法文译者则不那么批评,对海克尔的支持更为偏颇,热情地概述了人类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如何经历蠕虫、幼体海鞘、文昌鱼、七鳃鳗、鱼类等阶段,这一过程在化石记录中有所反映,见证了生命宏伟蓝图: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类,通过细胞分裂与分工实现进步。这种粗糙的重演论与海克尔的名字不公正地联系在一起。这点使海克尔备受批评。然而,最重要的是,支撑达尔文进化论中变异遗传的社会主义议题并未因那次交流而淡出视野。海克尔的批评者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 1840-1913)捍卫了达尔文主义的社会主义解读,这一观点在德国生物学界一直争议不断,直至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原因在于,反对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运动的作家们抓住了海克尔将选择理论描述为“贵族式”的特点,导致了对进化论的极右翼解读。因此,1877年的海克尔-菲尔绍辩论被视为德国社会达尔文主义发展的起点,后来成为德国优生学与种族卫生学的支柱。
1858年,海克尔与表妹安娜·赛特(Anna Sethe)订婚。在耶拿大学站稳脚跟后,1862年8月18日,海克尔与挚爱安娜交换了婚誓与戒指。然而,命运弄人,1864年2月16日,幸福婚姻尚未满两年,安娜的离世使这对伴侣天人永隔。海克尔悲痛欲绝,他通过更加投入的研究与写作来抵御抑郁的侵袭。那段时期的努力,从海克尔的痛苦深处孕育出了他的杰作——1866年的《普通形态学》。尽管这部著作远不及他1868年的《自然创造史》、1899年的《宇宙之谜》或1904年的《生命奇迹》等作品那样广受欢迎,但它不仅是海克尔在达尔文框架下整合当代生物学科学才华的见证,更对德国生物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紧随其后的是1874年发表于《耶拿自然科学杂志》的《原肠胚理论》,该理论对海克尔1866年发表的某些观点和思想进行了修订。
爱德华·S·拉塞尔(Edward S. Russell)在其广为人知的动物形态学历史著作中,将海克尔的《普通形态学》描述为“自然哲学的一个迟来的分支……是教条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形态学和进化论的混合体。”海克尔的传记作者罗伯特·J·理查兹(Robert J. Richards)认为,拉塞尔对海克尔作品的贬低评价,受到了拉塞尔自身对亚里士多德目的因的坚持以及对生命现象解释中粗犷唯物主义和机械论的厌恶所影响。《普通形态学》确实可以被视为一种革新精神的产物,旨在消除生物学中德国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残余痕迹,转而支持一种机械和唯物主义的生物及其演化观念。在海克尔写作的时代,“进化”一词(法语为évolution;德语为Entwicklung)仍具模糊性。最初,该词指的是胚胎或个体发育。但达尔文在1859年《物种起源》的最后一句话中,用该词来指代其带有修改的传衍理论。为了明确生物学术语,海克尔引入了“个体发育”(ontogeny)指代个体发展,“系统发育”(phylogeny)指代带有修改的传衍过程。海克尔主张,比较形态学不应满足于解剖成年生物体并寻找它们之间的理想联系,即概念上的纽带。相反,它应致力于根据个体发育来理解生物形态,因为只有这种综合的、动态的生物形态观念,才能揭示其系统发育的起源和关系。海克尔本人宣称,《普通形态学》体现了“我们职业的责任……坚决介入为科学自由和自然真理发现的神圣战斗。”然而,尽管海克尔本人否认,其《普通形态学》中仍明显留有自然哲学和唯心主义形态学的痕迹,如他所称的“生物晶体学”即前形态学(Promorphologie),以及贯穿所有生命的进步主义动力论,这既体现在个体发育中也体现在系统发育中。总体而言,该书展现了对概念和术语澄清的执着,同时迫切希望将生物科学的各个分支及其研究对象对立分类。它读起来几乎像是一次整理工作:盘点当代生物学的内容,澄清与分类,阐明与综合,简而言之,旨在建立一门系统结构化的形态学科学。《普通形态学》的副标题为:基于传衍理论的生物进化形态机械科学批判基础。海克尔将本书第一卷献给他的“尊敬的朋友和同事卡尔·格根鲍尔”,并以歌德的一段话作为引言,这段话安抚了德国唯心主义:**自然永远创造新的形态;现存之物前所未有;过往之事永不复返:一切皆新,却又永远是那旧有的。**歌德的影子贯穿全书始终,伴随读者阅读。
在引言中,海克尔强调,他将在因果律的基础上超越形态学与生理学之间的旧二元对立,并指出他早年在柏林时的导师约翰内斯·穆勒和维尔茨堡的鲁道夫·维尔肖——后者通过其细胞病理学——在他心中点燃了一元论的初始火花。**形态学家不应满足于对动物(及植物)形态的描述,而应致力于通过发展过程理解形态的生成。**海克尔摒弃了严格而纯粹的实证主义那种不加思索的事实收集策略,他认为这种策略往往迷失方向——特别是在植物学中——陷入关于物种划分的无谓争论,全然忽视了通过因果和历史关系联结起来的复杂整体视角。唯有当有机现象多样性中显现的普遍规律被认识并形式化后,形态描述的艺术才能提升为真正的形态理解科学。基于内在因果性的规律性认识,将技艺性的形态描绘转化为科学的形态学。宇宙由物质和力构成:没有不含固有力量的物质,也没有脱离物质、因而失去功能的力。这一点对于无机界与有机界同样适用。传统上,形态学被视为静态形式的科学,生理学则是动态功能的科学。然而,个体发育史或个体发生的研究,始终是形态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海克尔而言,正是通过个体发生的研究,比较形态学才与生理学最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格根鲍尔在耶拿求职谈判中极力主张的分离,被海克尔以一元论之名、作为统一因果原则的祭品而牺牲。海克尔采纳并完善了格根鲍尔引入的其他区分。他将形态学科学分为两大学科分支:静态的解剖学科学和动态的形态发生学。在解剖学内部,动物解剖学是分析性的,它整理事实;比较解剖学则是综合性的,它解释形态。形态可以从两条不同的路径进行分析和解释:一是考察生物如何由个体结构组件构建而成,海克尔称这一学科为构造学(Tectologie);另一条路径是原形态学(Promorphologie),研究构成生物整体形态的基本、基础形式的不变立体几何特性。然而,由于一切存在只有在其生成过程中才能被完全理解,动态的形态学观念必须补充成年生物的比较解剖学。这一动态的形态发生学进一步分为两个分支:个体的发育史或个体发生,以及集体的发育史或系统发育。
转向形态学与系统学的关系,海克尔对那些博物馆系统学家们嗤之以鼻,他们辛苦地为尘封收藏中的标本——针插的昆虫、浸泡的青蛙或是贴于植物标本册中干枯褪色的植物——逐一标注、编目,每一种都鉴定至种。在海克尔青年时期,“许多德国大学的动物学领域充斥着无脑的系统性工作”,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比较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的新发展逐渐盛行,“并在一份新期刊《科学动物学杂志》的创刊中找到了外在的表现形式。” 通过海克尔的工作,原本迂腐且无趣的“物种动物学”突然面临一个更为宏大的规划,虽寥寥数笔却勾勒得强劲有力。 海克尔抱怨道,生物学家中的系统学群体往往只关注生物的外表,对其详细的解剖结构、发育过程、生理机能、生活史及系统发育毫无兴趣。他声称,在自然界中,生物的外表与内在结构紧密交织,仅关注一方面而忽视其他,会导致对整体的错误理解。在海克尔看来,这导致了解剖学与系统学之间的分裂,损害了后者的发展。 比较形态学与系统学的目标不应是将物种多样性按人工体系进行解析排序,这种体系更像一个鉴定钥匙,而非传达关于真实的、即历史关系的知识。相反,形态学这门科学应致力于基于比较解剖学与胚胎学的综合,重建一个自然系统——这一系统力求展现系统学家所识别物种的系统发育,即种系树。海克尔认为,比较形态学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与系统学建立起富有成效的紧密联系。比较形态学以其静态与动态的研究方法,提供了破译物种间血缘关系(Blutsverwandtschaft)的工具。正是这些血缘关系将决定自然系统的结构,这一结构既能以系统发育树的形式呈现,也能转化为层级分明的术语与名称索引(Sach- und Namensregister),它不仅传达物种及物种群间的历史关系信息,还揭示这些物种及物种群的形态特征,这些特征本身又透露出系统发育的关联。
在《普通形态学》的前六十页左右阐述其议程后,海克尔引入了其形态学科学中的若干核心概念,这些概念需要更详尽的评论与分析,因为它们在此后数十年的系统生物学中持续产生重大影响。海克尔论点的核心自然是其一元论,由此衍生出科学统一的论断,反映了受自然法则支配的自然界的统一性。科学的任务是发现基于因果律原则的自然法则,这是一种物质主义和机械论的视角,反对在解释生命现象时引入任何辅助的生命力构造。其次是生物个体的概念,即历史的——与逻辑相对的——个体。海克尔引用了托马斯·H·赫胥黎对有机个体的定义,即“从受孕到繁殖过程中所有短暂发育阶段的生物体”。这样的有机个体可以由单一的生理个体代表,或者在经历世代交替的生物体中,由一系列生理个体代表。因此,从受孕到死亡的特定生物体,对海克尔而言,是生理个体的典范示例,但生物体的组成部分——器官系统、器官或细胞——又如何呢?反之,若从复杂性递增的层面考虑,动物群落、物种以及动物门(Thierstämme)的个体性又是怎样的?物种本身对海克尔来说是一个高度成问题的分类单元。自林奈以来,物种被视为比较生物学的基本单位。但正如格根鲍尔幼时在其母亲身边所经历的那样,海克尔也讲述了自己十二岁时如何徒劳地试图区分“好”与“坏”的黑莓和柳树、玫瑰和蓟的物种。物种是什么,应如何理解?无论博物馆分类学家告诉我们什么:如果达尔文是对的,物种在自然界中真的能作为离散且独立的实体存在吗?最后是自然系统,形态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如何从物种出发,通过不断扩大的物种群,直至乔治·居维叶和卡尔·恩斯特·冯·贝尔所识别的动物门,甚至更广范围,构建这一系统?整个生命是否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构建系统发育树并赋予其现实性的血缘关系(Blutsverwandtschaft)线索是什么?最棘手的是:如果这些系统发育或血缘关系本质上是历史的,因而不再直接可观察,它们又如何成为实证科学的对象?
本章节是对 Phylogenetic Systematics: Haeckel to Hennig 的部分翻译,如果有出版社感兴趣,欢迎联系 malacology.net ,版权所有禁止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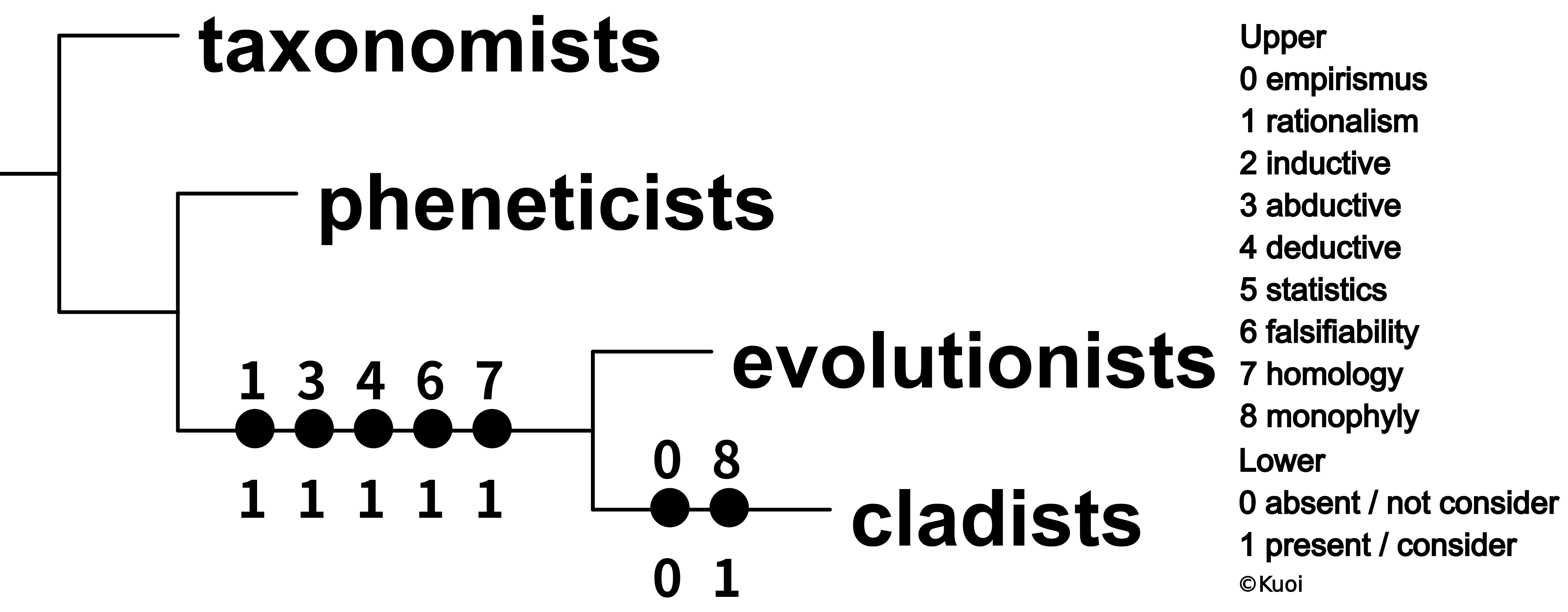

Comments
No comments yet. Be the first to react!